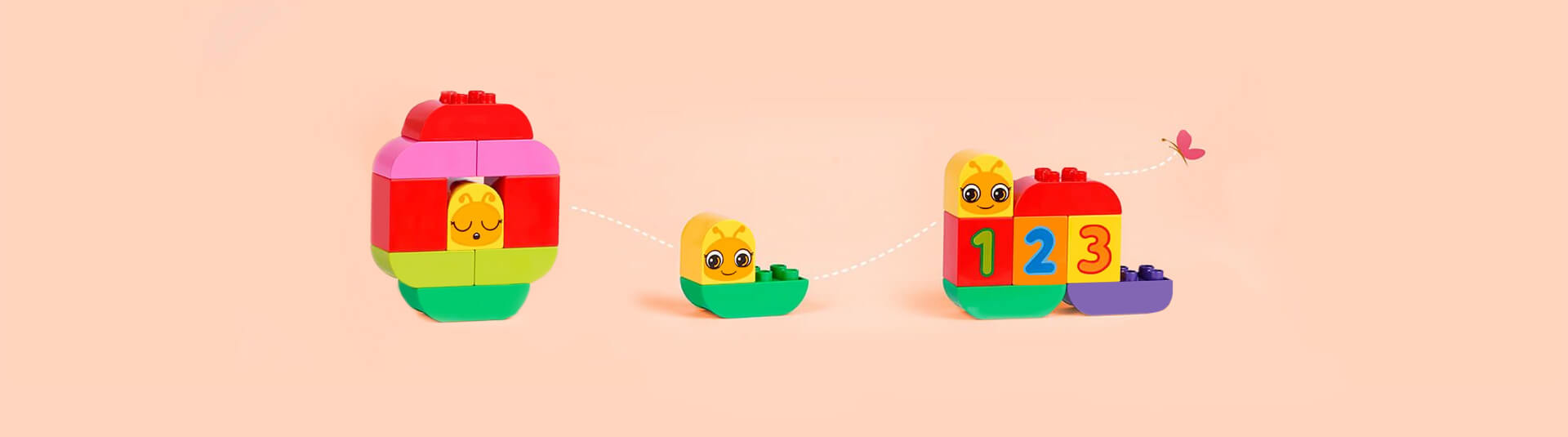产品说明

摘 要:羌姆袍是藏传佛教羌姆仪轨中的重要服饰,它以独特的“百衲”结构蕴含着深刻藏汉融合的宗教文化。文章采用实物与文献结合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对羌姆袍“百衲”结构进行释读。研究认为:①百衲结构在藏汉佛教的三衣、曲贵等僧侣服饰中多有体现,是具有深刻“苦修”象征意义的宗教图符,这种宗教图符在藏传佛教的羌姆袍中又有着“无量”的特点;②羌姆袍百衲结构既是藏传佛教“万物有灵”的精神寄托,又有着中华民族俭以养德的传统,是中华传统服饰结构形态天人合一精神内涵的藏族范式;③羌姆袍百衲结构既有对物的敬畏,又有对神的敬畏,既是僧服又是神服,其平面“回”字百衲形式具有以羌姆仪轨感召俗众的宗教普渡众生意义。
在藏地还普遍存在通过古老“羌姆”舞蹈形式弘传藏传佛教教义,并以此实施密宗仪轨仪式,具有丰富的藏文化传统,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姆①由艺僧表演,服饰除面具以外,最具标志性的就是羌姆袍,它是象征主尊和护法神的图符,藏语叫“朴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藏传佛教羌姆服饰保留了非常难得的原生形态,其中涉及到原始宗教、传统艺术、藏传佛教、民族融合等多种因素,因此整理分析羌姆袍结构是珍视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同时,通过对于羌姆袍结构的研究,可以发掘羌姆袍的文化特质,以期再一次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提供物质文化研究实证。
羌姆袍作为物质文化的载体,却鲜有对其结构和纹章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羌姆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失,有关羌姆袍的历史和宗教文化有待得到深度解读。在直接文献不足、缺乏详细的文献史料可考的情况下,以物证史、以图证史的物质文化研究尤为重要。通过实物、图像、文献的二重论据,认为羌姆袍有“出摆”“百衲”“大袖”三个标准形制,其中“出摆”有专家考证它源于明官服“盘领胸背纹章缯耳袍”,而羌姆袍所保存独特的“百衲”结构却成为羌姆文化的学术之谜。就此通过对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提供的羌姆袍标本的系统研究,结合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梳理,确有重要发现。
“百衲”就《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一、僧衣。‘百衲衣’的简称。百衲,谓补缀多。二、用零星材料集成完整的东西。”[1]“衲”揭示着佛教朴素的苦修思想,最早关于“百衲”的记载就与佛教有关,敦煌千佛洞上记载的变文——《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巧裁缝,能绣补,刺成盘龙须甘雨。个个能装百衲衣,师兄收取天宫女。”[2]与“百衲”相对应的概念是“拼接”,拼接在文献中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汉代,“拼”,在《尔雅》中的释义为“从也”;“接”,在《说文》中为“交也”[3]。拼接英文(joint)意为用碎片拼成整体,在古埃及古罗马都有所发现。拼接强调了事项的技法,更能表达百衲的意思,但弱化了背后的寓意和智化精神的追求,“百衲”所承载的宗教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是拼接无法比拟的。
在藏传佛教中,“衲”形象地记录着佛教僧衣对僧人修持的功绩,在亦俗亦教的藏文化中不断对世俗产生着影响,羌姆袍的“百衲”结构正是传递着这种信息。与汉传佛教的教俗分明不同,羌姆表演实施的弘法和密宗仪轨仪式是面向信众的,羌姆袍及其百衲的结构图符具有普渡众生的意义(图1)。
从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道开始,佛教法衣经历了从早期头陀时代的粪扫衣到部派时期三衣的发展演变。以粪扫衣和三衣为代表的佛教僧衣不仅是各宗派比丘形象的标志,更是佛教戒律和教义的外化和标志,具有深刻的宗教哲学。百衲衣可以说是粪扫衣到三衣的过渡形态。
在《大智度论》②中就有对衲衣的记载:“白佛当著何等衣。佛言应着衲衣。”[4]此处的“衲衣”便为“粪扫衣”,又名“弊衲衣”,由“世人所弃之朽坏破碎衣片”[5]制成,以弘扬佛理中对世俗欲望的舍弃,从而达到修行的目的,拼碎越多说明苦修越甚,最终衍生成三衣(汉传佛教的袈裟)的等级符号。
《僧祇律》:“三衣者,贤圣沙门标志。”[6]“三衣”根据“割裁条”制成田相法衣,分成三个等级,即僧伽梨、郁多罗僧和安陀会。“割裁条”中的长短条更多,比喻圣法增加而凡情减少,旨在坚定僧侣修持的决心[7]。在汉地,袈裟是佛教三衣的代名词。《佛衣铭》:“佛言不行,佛衣乃争。”[8]袈裟是正式的高僧法衣,且以奇数分为二十五条、七条和五条等级,成为禅宗师徒传法的信物(图2)。
公元7 世纪,三衣随着汉传佛教和印度佛教进入西藏,受西藏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曲贵”服制,主要变化是改变了“作净”③手法,即净修,增加了具有藏汉文化融合的“三角插片”与“中央图符”(喜旋纹为主,类似于汉地的太极图),曲贵在完成中华民族两大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一的藏传佛教僧侣服饰本土化的进程中是具有标志性的[9]。除曲贵外,在藏传佛教僧侣服饰中的达冈、堆嘎、香木塔以及羌姆袍等都有“百衲”的结构存在(图3)。
通过对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和西藏文化博物馆提供的羌姆袍标本的系统研究,结合国内外不同时期的图像和相关文献,梳理归纳出羌姆袍的两种结构形制:即上下分裁的上衣下裳制断腰式羌姆袍和上下连裁的通袍制直身式羌姆袍,其中直身式羌姆袍多用整幅料,衣身处的彩条后缀于其上,断腰式羌姆袍破整幅料,拼接与直身式羌姆袍相比较多(图4)。
上下分裁的断腰式羌姆袍有着纵向和横向拼接,纵向集中在大袖上,横向在胸部以下的衣身部分。通过对标本的梳理分析,结合大量的图像资料,总结归纳出断腰式羌姆袍的百衲形式为:四方对称。标本A和标本B即为这种百衲方式,大袖和衣身相互对应,也即十字方位东南西北的排列方式保持一致。图5 中是断腰式羌姆袍四方对称百衲形式的图示,上下的边缘和左右的边缘采用的质地、颜色一致,此后一一对应,严格遵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对称,呈平面“回”字形,突出“神”性。
通过对标本、图像、文献的梳理可知保持四方对称的平面“回”字形百衲方式多出现在清早期图像资料、传世绘稿和博物馆馆藏羌姆袍等古代图像资料中,故认为这种百衲形式是羌姆袍的原生状态,也是羌姆袍百衲形式的标准形制。随着历史的演进,羌姆袍有着多种百衲方式,这种四方对应及排列方式逐渐模糊,但羌姆袍百衲结构形制的整体特征保持不变。
直身式羌姆袍的百衲分为有规律横纵向拼接和无规律拼接两种情况,根据梳理出的羌姆袍图像资料,认为直身式羌姆袍的彩条状拼接是后缀于整幅袍料上,不会破坏整幅料,直身式羌姆袍多用龙纹、蟒纹,且在整幅使用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破坏龙纹、蟒纹的情况。
综上,羌姆袍百衲的规律有:断腰式羌姆袍遵循四方对称的平面“回”字百衲形式;直身式羌姆袍大袖有有规律和无规律两种百衲形式;无论是断腰式羌姆袍还是直身式羌姆袍,大袖一定有拼接。
根据实物研究发现羌姆袍呈现出多处拼接的显著特点,但并不强调像高僧法衣曲贵(田相)“割裁条”的等级数量,而是强调“百衲”形态的“无量”,显然它在暗示跳出了凡界,所以羌姆袍的百衲结构正是象征主尊和护法神的“图符”。通过对博物馆馆藏标本进行测绘和结构图复原,结合图像文献整理发现,无论是断腰式羌姆袍还是直身式羌姆袍都遵循有序和无序这两种百衲方式,并呈现出有序和无序相结合的样式。此外,在对标本信息的采集、整理过程中,发现羌姆袍的结构形制并未脱离中华传统的十字型平面结构④。
标本A为上下分裁的断腰式,全长125cm,通袖长146.7cm,袖宽77cm,呈现出对襟、无后中缝、大袖、有出摆、出摆内有褶裥、百衲的特点,颜色以黄、红、褐色为大宗,通身由植物纹和几何纹组成,其中莲花纹、牡丹纹、菊花纹居多。标本A 为有序拼接的百衲形式,上衣身是一个整体,由两种有特定纹样的面料构成。全身共由48 块拼接而成,下裳为10处拼接,阔袖由22个条状布拼接而成,左右呈对称分布,条宽为7.5cm左右,另左右侧缯耳的褶裥各拼接10 处,面料共有十二种,纹样均为植物纹样,且都遵循十字型平面结构的对称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横纵向规律拼接内又有无序拼接的现象,显然是物尽其用的节俭考虑(图6)。
根据陈国权《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专业报纸因致力于细分市场,读者对象更明确,总印数降幅较小,市场前景良好。但面对“互联网+”模式的冲击,专业报也融入新媒体中,深挖读者需求,谋求进一步发展。根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团队完成的《2017年中国新闻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传统纸媒发展和转型形势依然严峻。相比于党报、专业报,综合商业报由于缺乏政策红利、盈利模式相对单一、新型收入探索艰难、服务功能更易被网络所替代等原因,转型面临诸多困难,相继停刊。因此,综合商业报必须攻难克坚,在2017年继续与新媒体融合,寻找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从整体上看,党报在2017年与新媒体融合方面成效显著。
标本B亦为上衣下裳制的有序拼接百衲结构,全长141cm,通袖长158.9cm,袖宽97cm,有着对襟、直领、无后中缝、大袖、有出摆、出摆内有褶裥,百衲的结构特征,颜色主要为黄、红、褐色,纹样为寸蟒纹,尾襕处有四条行龙。全身共有60处拼接,几乎无整幅面料的使用。上衣由2片宽度不等的相同面料拼接而成,阔袖有28 条状拼接,宽度约为8cm,左右排列和数量基本对称,是在节俭前提下以百衲形式诠释苦修的又一侧证。同标本A 一样,在同色系横纵向规律拼接内又存在无序拼接。通过对两例标本的百衲结构研究发现,无论是衣身还是袖子,它们的拼接缝多表现为布边,这意味着在“割裁条”时充分利用布边,而使面料利用率达到最大,可谓节俭理念的物化体现。面料主要有7 种,且前后底襕处均有两条对称行龙,据史料和图像资料可知明清两代多在膝襕、底襕置龙纹、蟒纹、麒麟等纹样,羌姆袍在底襕处设行龙或是仿制明清官袍而来(图7)。
通过对标本A和标本B的分解,对同一种面料的排列发现羌姆袍的裁剪方式遵循“交窬”这种古老裁剪方式,这种裁剪方式在藏袍和北大秦简中都有发现,其巧妙地利用交错互补的目的就是节俭[10]。羌姆袍中的这种裁剪方式也表现出“人以物为尺度”的自然有灵观,既是对物的敬畏也是对神的敬畏,体现出了藏族先民“敬物尚俭”儒道思想的汉文化传统和“万物有灵”藏传佛教理念在服饰上的同构。
标本C 为上下通裁形制的无序拼接百衲结构。全长121.5cm,通袖长174.7cm,袖宽80cm,结构特征为圆领、对襟、有后中缝、大袖、有出摆,摆内有褶裥、百衲。标本衣身无明显拼接,仅在袖子表现为无序拼接的百衲结构,呈现出整幅面料和碎拼面料相结合的特点。根据化零为整的方法解析标本,发现衣身和袖子的分界线一定是有布边的,说明主体衣身一定会用整幅,布幅在60~70cm,与晚清手工布幅标准是相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标本C袖子大量不同面料的无序拼接看似杂乱无章,对其结构的综合分析却有玄机。衣身由两种龙纹面料组成,一种为整幅使用的衣身主体部分,一种作为袖子和出摆褶裥处拼接,共24 处。作为阔袖部分是一分为二的,外侧部分独立出来的袖子用于表现“百衲”的宗教符号,由于面积变小也就采用了边角余料自由拼接形式,它的理念来源于以节俭的“敬物”方式转化为对神的敬畏符号,因此缩小的百衲图符更强调了她的宗教徽帜(不宜过大),且羌姆袍破龙纹的百衲方式更是对“万物有灵”的有力诠释。但这不意味着以放弃“仪式”为代价,恰恰相反,从还原的标本结构图发现,在身和袖连接的衣身一边有四个对称的拼角,衣身主体还有硕大的二龙戏珠和立水的皇家图案,故可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由清帝向藏贵的赐服改制成羌姆袍;二是带有皇家御制的羌姆袍。从结构形制和百衲徽帜特征看更像后者:原因一是侧耳的形制是羌姆袍特有的;二是百衲结构的有序和无序是精心设计的;三是整体的前二、后二和肩二的六个行龙纹是在中缝和肩线十字型坐标中对称布局的,显然这是藏汉文化融合的产物(图8)。
布幅决定服饰的结构形态[11]的中华服饰系统并没有在羌姆袍百衲结构的碎拼中消失,因为这种结构形态就是因节俭而生,它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因此“节俭”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这就是整裁整用在羌姆袍中的充分体现。研究表明三个标本无论采用有序百衲还是无序百衲,它们的衬里结构都是采用最节俭的整幅“割裁条”手法,由此可见羌姆袍的百衲结构(节俭意念)是神赋予僧众时刻苦修的戒牒(图9)。除衬里外,直身式羌姆袍的衣身主体也是采用最节俭的整裁整用手法,可谓万物有灵的物化体现。
在藏传佛教的生命哲学中,所有的器物都是不能永恒固定的一种幻相。羌姆袍是具有象征性仪式性的宗教服饰,具有原始宗教和理性宗教双重特性,其意义并不在于服饰本身,而在于通过它所获得的精神力。百衲是“相”与“精神力”之间联系的载体,是超越形式语言的存在。百衲表面上是一种器物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下沉的修行方式,它的表达背后有更高维度的精神力,就是“百衲”既有着对物的敬畏(用节俭的方式表达苦修),又有着对神的敬畏。
通过对羌姆袍百衲结构的分析发现,与藏族人民“表尊里卑”的朴素美学所不同的是,羌姆袍内里结构较为完整,而外在结构则出现多处拼接。结合文献、图像和实物标本发现,大部分羌姆袍的百衲呈平面“回”字形,即十字方位东南西北保持对称(图10),笔者认为这种百衲形式所构成的空间形式,暗含了藏传佛教曼荼罗的观念。
图10 平面“回”字形百衲的羌姆袍(来源:《一位19世纪的西藏绘制的喜马拉雅山地图:探索之旅》⑤、私人收藏家冯一明、《中国藏族服饰》)
羌姆被称为动态曼荼罗。以桑耶寺为例,桑耶寺羌姆的本质是曼荼罗,其夏季羌姆所依原始脚本经文全名为《上师密集曼荼罗仪轨简明注释》,僧人们在实际操作时所用脚本,是依其制作的便捷版本[12]。另羌姆表演中的“色仗”,僧众仪仗出现时,僧人手中的立体曼扎,亦可理解为法器类立体曼荼罗。基于羌姆的脚本、角色、结构和形式中“曼荼罗”特点考虑,认为羌姆袍的“回”字百衲形式也是羌姆仪轨呈现“曼荼罗”的一部分。
曼荼罗是梵文Mandala 的音译,是佛教宇宙观的承载体,也被称为坛城。藏密坛城主要以圆形和正方形为主,圆形符号表现时间观念,方形符号构成空间结构。极为对称并且都有中心点,以对称和规律的构造方式来表示佛教宇宙世界的庄严秩序。“曼荼罗”最初是为防止魔道入侵而筑起的方型或圆型土坛[13],多层次的方形空间形式象征着众佛的加持,以达到驱魔的效果(图11)。羌姆袍的曼荼罗空间观,就体现在其通过符号形体传达出的讯息,这个符号形体便是横纵向对称分割,也即平面“回”字形百衲形式。从图像信息来看,羌姆袍的平面结构和坛城构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羌姆袍也呈十字型对称和四方对称。驱魔祈福也是羌姆表演的目的之一,羌姆袍的横纵向拼接的百衲形式也为魔鬼设置了一道道的屏障。
图11 曼荼罗(图片来源:蔡东照《佛教美术全集16—神秘的曼荼罗艺术》)
羌姆袍的穿着主体主要是护法神,护法神是维护藏传佛教免受敌魔侵扰且具有力的神灵[14]。在羌姆仪轨中,戴着骷髅面具的魔王时常会来人间进行破坏,他们所作的恶象征着地狱、畜生、饿鬼。而随后出场的护法神等将其进行,达到护卫佛法庇佑僧人信徒、邪魔鬼魅的目的。在举行羌姆仪式时护法神所穿的法衣和使用的道具更是具有非凡的力量。绝大多数护法神头戴人头骨冠,身穿大袖羌姆袍,以幻化的形象视人,面目威严、青面獠牙,手执各种人体器官制成的法器,腰扎人头串珠,或身绕毒蛇,表示对妖魔的[15]。这种夸张、狰狞,具有威慑性的装扮,既表现着对神的敬畏,同时意味着摧伏魔怪的威力,弘扬佛法的大德。羌姆袍呈十字型对称,两袖部分及前后衣身部分及中点表示东西南北中五方,藏传佛教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有一佛主持,即五方佛,多层次的方形拼接空间形式象征着众佛的加持,可以说羌姆袍的横纵向拼接的百衲形式为魔鬼设置了一道道的屏障,以众佛的加持达到调伏邪魔、驱魔祈福的目的。由此可见,羌姆袍象征着对神的敬畏,从而达到镇魔、普渡众生的宗教功能。
羌姆袍“百衲”结构围绕着的,是中华民族造物的集体意识。在一个完全自然经济的历史时期,造物的不易,会普遍认为是神赐,羌姆袍百衲结构对物的敬畏通过宗教的力量得到仪式化,这是中华传统服饰结构形态诠释天人合一精神内涵的藏族范式。藏传佛教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追求人以物为尺度的自然有灵观,保持物的原生态,羌姆袍百衲结构既是节俭的需要,又是“万物有灵”的精神寄托,在教义上既有着对物的敬畏,又有着对神的敬畏。基于“百衲”节俭计算的羌姆袍体现了万物皆灵观的原始思想,这种思想与汉族天人合一的“敬物”传统不谋而合,也就是敬物尚俭儒道思想的汉文化传统与万物有灵的藏传佛教理念在服饰上的同构,羌姆袍的百衲结构形态正是实证。这种人以物为尺度的天人合一中华正统,在羌姆袍百衲结构中始终坚守着,即便到了今天这种基因依然存在。
羌姆袍作为具有象征性仪式性的宗教服饰,其平面“回”字百衲形式暗含了藏传佛教曼荼罗的空间观,突出了“神”性。羌姆袍平面“回”字形百衲形式是羌姆仪轨中护法神的宗教图符,层层的条形拼接空间形式象征着众佛的加持,既表现着对神的敬畏,同时达到调伏邪魔、驱鬼祈福的目的,意味着众护法神跳出了凡界,沟通人神。羌姆袍的百衲结构既是对物的敬畏也是对神的敬畏,既是僧服,也是神服,具有以羌姆仪轨感召俗众的宗教普渡众生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